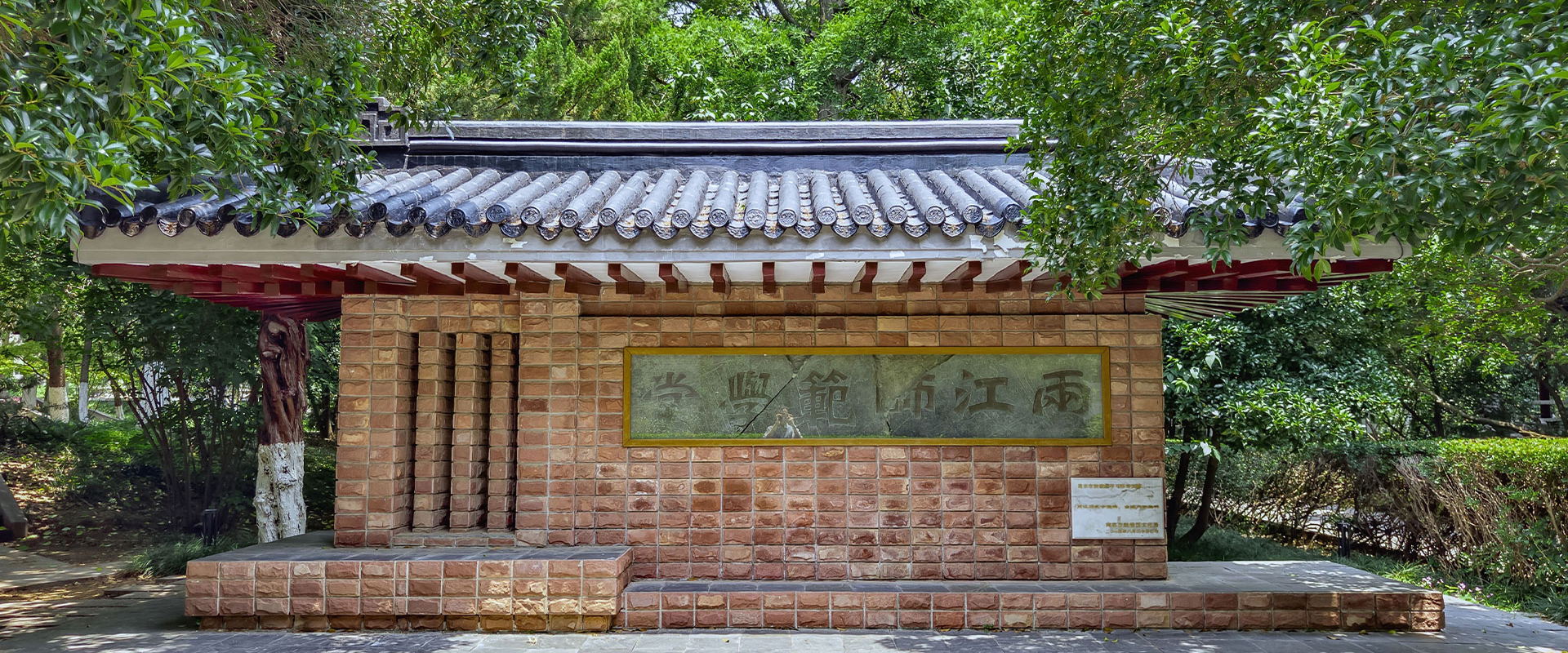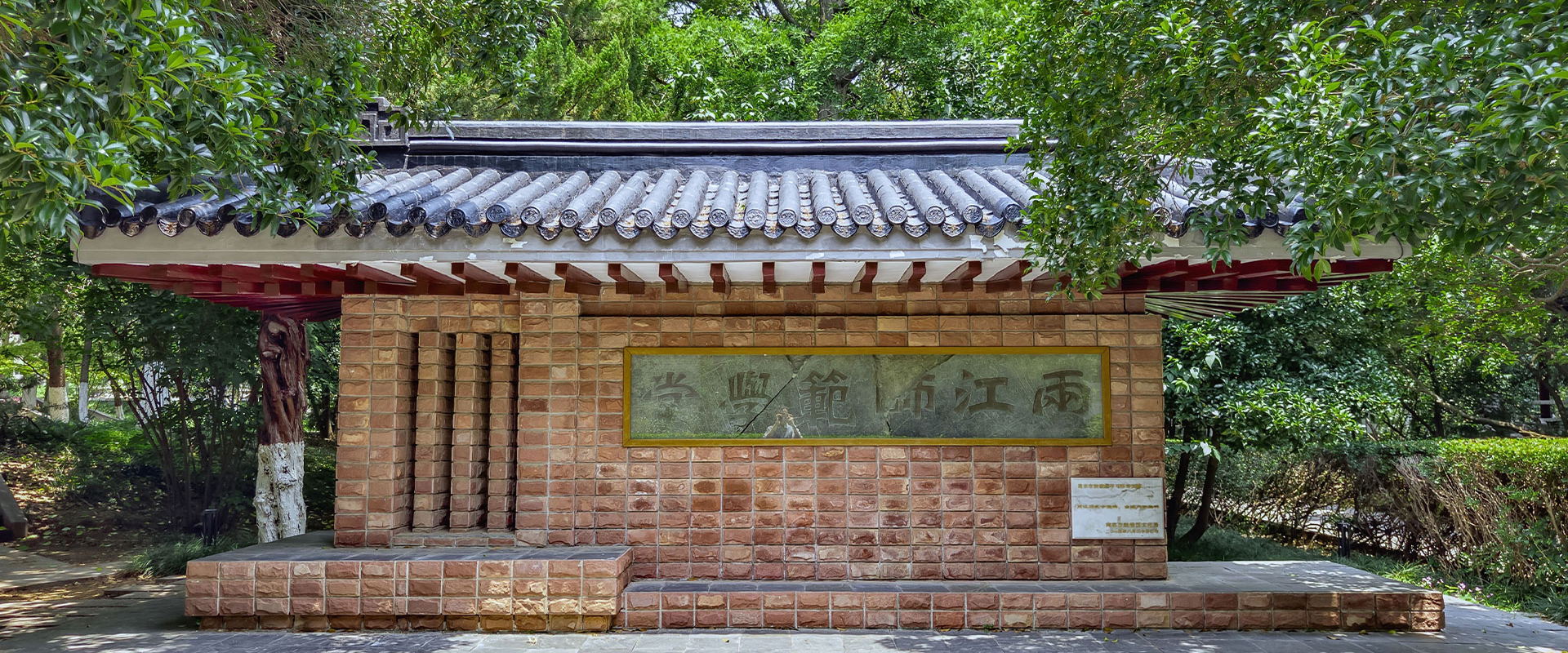南京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助理研究員李國(guó)成在《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》2024年第7期發(fā)表《人工智能文學(xué)及其對(duì)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的挑戰(zhàn)》一文,從后文學(xué)與后人類(lèi)的視角對(duì)人工智能文學(xué)的歷史���、挑戰(zhàn)和潛能進(jìn)行了探討�����。
首先��,論文指出�����,人工智能文學(xué)作為文學(xué)與科技相結(jié)合的新形態(tài)����,根據(jù)采用的技術(shù)路徑的不同而具有順序范式和連接范式兩種類(lèi)型、兩個(gè)階段��,近年來(lái)人工智能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的突破有賴(lài)于人工智能技術(shù)路徑的轉(zhuǎn)換所帶來(lái)的深度學(xué)習(xí)和神經(jīng)網(wǎng)絡(luò)技術(shù)的迅速進(jìn)步����。然而,從文學(xué)史的角度看���,人工智能文學(xué)的創(chuàng)作機(jī)理在人類(lèi)文學(xué)活動(dòng)中早有萌芽�,并與20世紀(jì)多種先鋒文學(xué)實(shí)驗(yàn)相應(yīng)和���,自動(dòng)性����、隨機(jī)性���、程序性等人工智能文學(xué)的基本特征也正是超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的“自動(dòng)寫(xiě)作”����、達(dá)達(dá)主義的“剪切技術(shù)”以及潛在文學(xué)工坊的“限制寫(xiě)作”等所嘗試和追求的目標(biāo)。從某種程度上講��,人工智能文學(xué)是對(duì)這些先鋒文學(xué)實(shí)驗(yàn)內(nèi)在訴求的回應(yīng)����。在應(yīng)對(duì)20世紀(jì)初以來(lái)傳統(tǒng)文學(xué)的危機(jī)中����,先鋒文學(xué)運(yùn)動(dòng)所設(shè)計(jì)的各種文學(xué)效果在計(jì)算機(jī)和人工智能技術(shù)條件下能夠得到更為便利和豐富的實(shí)現(xiàn),這表明我們不宜簡(jiǎn)單粗暴地貶黜人工智能文學(xué)的意義和潛能���。
其次�,論文討論了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對(duì)人工智能文學(xué)的各種批評(píng)����,并分析了這些批評(píng)中的富有爭(zhēng)議之處。人工智能文學(xué)是20世紀(jì)后半葉以來(lái)后文學(xué)和后人類(lèi)狀況下的新現(xiàn)象����,但人們?cè)u(píng)價(jià)的標(biāo)準(zhǔn)卻往往是17����、18世紀(jì)建立在作者中心主義基礎(chǔ)上的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���,這是一種應(yīng)當(dāng)認(rèn)真審思的重要錯(cuò)位��。事實(shí)上�����,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只是一定歷史條件下對(duì)文學(xué)的一種特殊認(rèn)識(shí)���,并非揭示了文學(xué)永恒不變的本質(zhì)。在20世紀(jì)中后期這一人工智能文學(xué)誕生和發(fā)展的時(shí)期����,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也遭受了劇烈的沖擊,以至于“作者死亡”“文學(xué)終結(jié)”的宣言層出不窮�。論文主要從三個(gè)核心要點(diǎn)考察了人工智能文學(xué)在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下的爭(zhēng)議:第一,情感問(wèn)題��?�!扒楦小笔抢寺髁x運(yùn)動(dòng)賦予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的核心要素��,也被認(rèn)為是人工智能文學(xué)難以表達(dá)的內(nèi)容。但20世紀(jì)以來(lái)影響巨大的文學(xué)客體論主張削弱甚至排除情感在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和研究中的作用����,而阿蘭·托梅的研究也指出,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中的“情感表現(xiàn)論”含有一種謬誤推理����,從文本的情感特征僭越地歸因到作者的情感體驗(yàn)。如果情感只應(yīng)在文學(xué)的文本特征中表現(xiàn)和把握���,那么就為人工智能對(duì)文學(xué)文本情感特征的深度學(xué)習(xí)和模仿創(chuàng)作提供了空間。第二���,靈感問(wèn)題?����,F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對(duì)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的靈感和創(chuàng)造力極為推崇����。而檢視人類(lèi)的文學(xué)活動(dòng)史�����,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并非一直以來(lái)都僅依靠天才和靈感,如荷馬史詩(shī)等早期人類(lèi)文學(xué)作品即是編織而成���,而非個(gè)人靈感的產(chǎn)物����,到了20世紀(jì)���,“編織”觀念又重新復(fù)興�����,作家再度被提倡和定位為各種書(shū)寫(xiě)的編織者��。第三�����,作者問(wèn)題�����。情感和靈感問(wèn)題都導(dǎo)向了作者問(wèn)題�,對(duì)人工智能文學(xué)的爭(zhēng)議的關(guān)鍵也在于此�。但作者及其創(chuàng)作方式歷來(lái)受到技術(shù)條件的限制和建構(gòu)���,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基于印刷術(shù)塑造的文化狀況,既不符合此前口語(yǔ)文化下的文學(xué)活動(dòng)特征��,也無(wú)法恰切地應(yīng)對(duì)當(dāng)今的數(shù)字文化所造就的文學(xué)新變��。
再次�,論文提出應(yīng)從后人類(lèi)視野來(lái)重新考察人工智能文學(xué)的本質(zhì)與潛能。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之所以遭受人工智能文學(xué)的嚴(yán)重挑戰(zhàn)�����,是因?yàn)樗诘淖髡咧行闹髁x是一種人類(lèi)中心主義��,而人工智能文學(xué)則是后人類(lèi)狀況的產(chǎn)物����。進(jìn)入后人類(lèi)狀況后�����,我們應(yīng)從人類(lèi)中心主義/主體中心主義立場(chǎng)轉(zhuǎn)換到更符合實(shí)際的人機(jī)協(xié)作的賽博格立場(chǎng)����。一般所認(rèn)為的“圖靈式人工智能文學(xué)”從根本上是人類(lèi)中心主義話語(yǔ)的變形��,在目前的技術(shù)條件下也尚未實(shí)現(xiàn)�����;當(dāng)前技術(shù)所實(shí)現(xiàn)的仍是“利克萊德式的人工智能”���,它從屬于賽博格話語(yǔ),是人與機(jī)器的非中心化的合作與共創(chuàng)����。如果我們從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活動(dòng)整個(gè)流程著眼,既重視人工智能的自主性���,又正視其對(duì)人的依賴(lài)性����,那么�����,人工智能文學(xué)毋寧說(shuō)是一種非中心化的“賽博格文學(xué)”��。它不是人工智能主體的自我表達(dá),而是與人機(jī)共生的賽博格信息系統(tǒng)相匹配的全新形態(tài)�����。從這一角度出發(fā)���,人工智能文學(xué)就不再是另一文學(xué)主體所產(chǎn)生的拙劣模仿和潛在威脅��,而是作為賽博格的人類(lèi)的完整能力的表達(dá)方式�����,能夠極大地拓展文學(xué)的概念空間和表現(xiàn)形式��,在人類(lèi)視角與機(jī)器視角�����、作者與讀者�、語(yǔ)言文本與非語(yǔ)言文本等方面具有跨界潛能����。
同時(shí)����,論文也強(qiáng)調(diào)���,盡管人工智能文學(xué)的“后文學(xué)”特征使之不宜再以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觀念的描述性概念進(jìn)行評(píng)判,但這絕非是說(shuō)應(yīng)拒絕任何傳統(tǒng)的規(guī)范性文學(xué)觀念對(duì)人工智能文學(xué)的指導(dǎo)�。對(duì)待人工智能文學(xué)的“后人類(lèi)”態(tài)度也不是要徹底取消對(duì)人類(lèi)自身的關(guān)懷,而是試圖在新的歷史背景下�����,以更切中現(xiàn)實(shí)的廣闊視野重新審視和關(guān)切人的存在狀況��,并由之為人類(lèi)謀求更好的未來(lái)����。人工智能文學(xué)作為海德格爾所批判的“語(yǔ)言機(jī)”的產(chǎn)物,是融危險(xiǎn)與機(jī)遇于一體的“雅努斯的雙面神”���,需要我們?cè)谄浒l(fā)展中不斷地加以追問(wèn)和反思���。